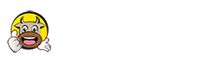中国文学期刊的读者们应该意识到最近出现的一个现象,众多期刊都高调地举行了创刊多少多少周年的庆祝活动。

这是好事,共和国早已度过了60华诞,从“文革”结束后开始的新时期也已接近40年,很多文学期刊的出版都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。今天回望一下走过的路,检阅一下曾经发表过什么值得怀念的作品,在文学边缘化、文学期刊发行量大幅度下降的当下,也可以起到一点鼓舞士气的积极作用。越来越多的期刊开始从事周年庆,各家期刊的贺电贺信你发给我,我发给你,已经成为当下文坛之一景。
但是,我发现,也许是历史漫长,已经经过了几代人变迁的缘故,有的文学刊物其实对自己的历史已经搞不大清楚了,这给它们要搞的周年庆增加了困难。曾记得1999年,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登出一个启事,说是为了庆祝该刊创刊50周年,要寻找刊物的忠实读者发给重奖,条件是必须拿得出该刊1949年的创刊号和1975年的复刊号。1949年虽然已经相隔久远,但只要这个创刊号存在,即使经历了“文革”那样的灾难,相信普天之下一定有人藏着这个稀世之宝。但是,要人拿出1975年的复刊号却是不可能的事,因为《人民文学》在“文革”中的复刊号是1976年1月出的,封面上标着的也是“1976年第1期”。看到这样一个启事,我当即致电《人民文学》编辑部,该刊一位接电话的先生听我讲了这个事情以后,不以为然地回答我:“我们一些老同志回忆他们是在1975年参加复刊工作的,怎么会错呢?”是啊,1976年1月出复刊号,当然要在1975年就开始工作喽。于是,这场寻找忠实读者的好戏,由于该刊自己的不忠实,只能悄悄收兵。
今年,该刊又准备庆祝创刊65周年了,刚刚出版的今年第一期已经开始了热身,在其卷首语上写道:“今年,我们把过去本刊的名篇插图处理成封面内容,在本刊65周年的特别年份,激励我们持续地推出精品力作。”读者朋友,你有没有发现这句话读不大通?别以为我在引用这段文字时漏掉了两个字,“本刊65周年”,这个算什么话呢?相比于要人拿出1975年复刊号的乌龙事件,这自然不算什么,让我们先祝福《人民文学》创刊65周年庆祝活动圆满成功。
文学期刊的工作人员,自然都是文人,而文人有一个天下通行的毛病就是懒散,像中国古代的“竹林七贤”放浪形骸,如果是普通人是要被关进收容所的,但因为是文人就成了千古美谈。但是,文人因为懒散,就不像档案馆里的工作人员一样,将一片纸、一行字都珍藏着,而是随用随丢,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从文学期刊里流出来的作家手稿。但是,这样一来,当他们想起要搞周年庆的时候,就只能借用文学创作的手法,搞形象思维了。去年年底,《上海文学》搞了一个庆祝创刊60周年的活动。我看到这条消息后,对此提出了疑问,以“欧阳琴川”的笔名,在去年12月19日的上海《东方早报》发了一个短文,对此提出质疑,认为《上海文学》创刊至2013年只有36年历史。我的理由是,《上海文学》2013年第12期标的总期数是434期,按其一年出12期刊物推算,它应该是在1977年创刊。《上海文学》的主办单位上海作协在1953年办过一本《文艺月报》,很显然,他们是把这本《文艺月报》当作自己的前身了。但是,《文艺月报》在1959年即已停刊,改出《上海文学》,而当时的《上海文学》在其封面上清清楚楚地写着“总第一期”,说明主办者是新办了一个刊物。而这个老的《上海文学》办到1964年就因为与《收获》合并而停止出版了。看来,现在的《上海文学》是按照鲁迅先生的教导,把这段与它并没有关系的历史“拿来主义”了。
这篇短文发表以后,据说《上海文学》杂志很不满意,该刊社长助理张予佳先生在12月27日的《东方早报》发文《〈上海文学〉创刊至今确实是60年》,对我的质疑提出回答。但是张先生是怎么回答的呢?张先生回顾了从1953年《文艺月报》到如今的《上海文学》漫长的60年历史,但是他却篡改了历史事实,将1959年《文艺月报》停刊、旧《上海文学》创刊说成后者是对前者的改名,将1977年新《上海文学》(当时叫《上海文艺》,1979年改为现名)的创刊说成了复刊。其实,对于这些刊物是停刊还是创刊或者复刊,只要翻开当时的杂志一看就一目了然了。
更让我不能接受的是,为了回答我关于总期数的疑问,张先生不惜伪造了一个法规以示其真理在手。他说,“现在《上海文学》标示的总期数,是根据国家出版方面的法规执行的排序标识,只表示‘文革’复刊至今这一历史时期的出版期数。”看到这样的说法,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。如果国家真有这样的法规,那么我们应该要给《上海文学》送上遵纪守法的大红花,因为全国大概只有它这一本刊物执行了这个法规,即使是与它同处一个作协大院里的《收获》杂志,也在违法乱纪,因为它标示的总期数就把“文革”以前出版的各期一起算进去了。
我在那篇短文中说:“无论是1977年《上海文艺》创刊号上的‘创刊词’,还是1979年更名为《上海文学》后的‘告读者’一文,都没有说过这本刊物是承接‘文革’之前《文艺月报》或者《上海文学》的历史……”张先生回答我说:“上世纪70年代末,‘文革’阴影犹存,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历史沿革的表述须慎之又慎,能回避的一定是尽量回避,这是特定时期的表述方式。”不知道张先生的年龄有多大,我想,每一个“上世纪70年代末”的过来之人看到他这样描述当时的历史,都是不能答应的。当时,在“两个凡是”的思想禁锢被粉碎以后,思想解放运动一浪高过一浪,而作家的思想解放无疑是走在了前列,出现了一大批直到今天还有其影响力的优秀作品。《上海文学》如果真是沿袭“文革”前的刊物接续出版,何来害怕之说?与其同处一院的《收获》不就是宣称复刊的吗?谁也没有听说这本刊物因此而惹上了什么麻烦。《上海文学》口口声声说这本刊物是巴金创办的,我想,巴老如果泉下有知,听到他的后辈如此看待他曾经呕心沥血的那个时代,也是不会答应的。
其实,读者认可一本文学刊物,决不是看它活了多少年,在文学阅读上,并不存在“尊老”这个传统。差不多与《上海文学》的这个虚假庆典同一时间,另一本文学刊物《十月》举行了庆祝其创刊35周年的活动。这本刊物策划了一个35年来在该刊发表的最具影响力作品的活动,白桦的《苦恋》,高行健的话剧剧本《绝对信号》、《车站》和贾平凹的小说《废都》都榜上有名。熟悉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读者都应该知道,这些作者和这些作品都引起过巨大轰动,有的出现了很大的争议,有的作家则已在中国文坛上销声匿迹。这本刊物能够在一次庆典活动上重提这些作家和作品,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,这本刊物也因此而能够受到读者的欢迎。
其实,在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里,《上海文学》也曾经发表过令人难忘的优秀作品。但是,既然这本刊物只是忙着60周年大庆而对它在上世纪70年代末真正创刊初期的那段历史视为“能回避的一定是尽量回避”,想必它对那段历史和它曾经发表的优秀作品也不屑一顾了。
由此可见,对于文学期刊来说,各种周年庆活动只是一种噱头,真正吸引读者的还是精彩的作品。更多新闻请继续关注广告买卖网。
 客服热线:400-966-0803
客服热线:400-966-0803